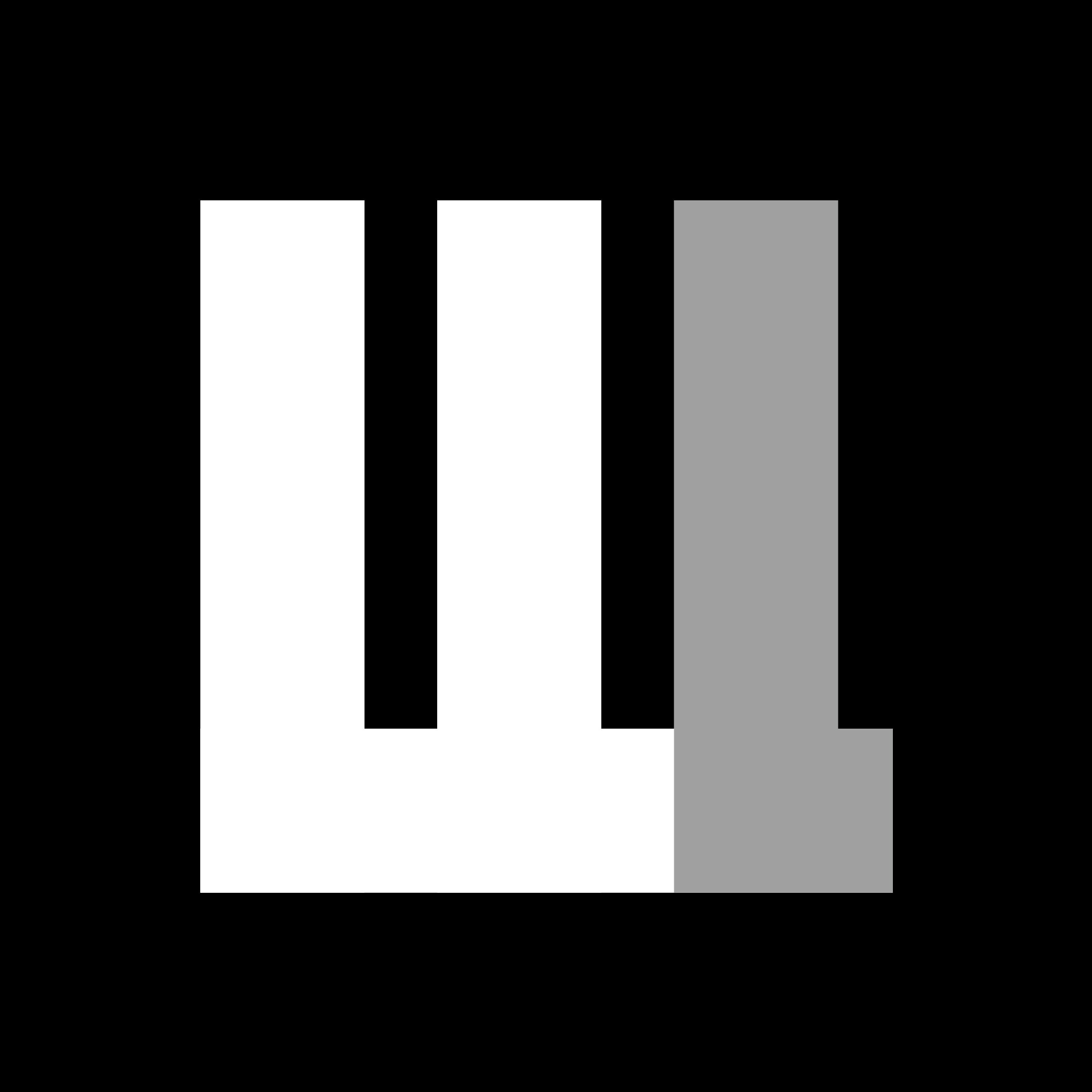三個奶奶
在秋天;一個奶奶死了,她有三個兒子,她有三個兒媳。
葬禮上;它有一口棺材,它有三個賬本,它有三個會計。
中毒
眼睛與嘴巴掛滿泥濘,目露血絲。
跌跌撞撞,跌跌撞撞。
牙齒叼住尾巴,打著滾: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頭頂住地面,蹬著後腿畫圓:
一圈,兩圈,三圈,四圈。
扎入結冰的泔水桶,沉入桶底:
一米,兩米,三米,四米。
第二个黑夜
在這裡穿過一個黑夜等待另一個黑夜來臨。
我坐在一張床的一角讀春天,兩腳發冷。
一個孩子就是一個國王,吵吵鬧鬧,晚間劇目正在上映。
變雪白的牆,和它中間雪白的沒有扇葉的鑽石牌吊扇。
扁平嘴巴的矮腿狗,嘴還是那麼扁腿還是那麼短。
扯破座子露出海綿的輕便摩托車倚著牆壁打點滴,身上蓋滿雜草。
踩滅髒水澆過結冰的地上的第四根中南海香煙。
過期五個月的鐘樓啤酒。
滿是青椒大盤的魚香肉絲。
燉糊了的蕃茄鮁魚。
九個人的全家福。
一張五十元,一張二十元,一張五元
元宵節.
臨晨四點.
我走出四號車廂.
我打個哈欠,抹掉眼屎.
準備去見一個朋友.
我故作老練的打車,故作老練的結帳下車.
我給你破舊的一百元真幣.
你找我嶄新的七十五元假幣.
( 紀二零零六年元宵節濟南)
石家莊
石家莊,你好。
穿過一段碎片
鬧鐘響起,在昨天相同的時間點。我起床不早不晚。
沿著通惠河快走著,穿過遛早的大伯大媽和他們都寵物狗,穿過一個或兩個的上班男女,他們的對話和氣味隨著風,在耳邊呼呼而過。
擠上每天的早高峰地鐵,無聲地擠,默契的擠,人們都懶得說“我的腳”“擠啥啊”,最多來句“哥們,慢點擠”和被擠時慣性發出的哎哎呀呀的聲音。
四惠,八點三十五。穿過通惠河的人行橋,裝修維修的手藝人在等待早晨的第一單生意;四惠橋建材批發市場,頭髮蓬鬆的保安裹著齊腳的大衣在夢遊。
穿過民居,穿過公共廁所;又穿過一個公共廁所。穿過雞店與妓店,穿過早點攤的熱氣與倒尿盆的熱氣交織的空氣中,穿過火車道口。
穿過百子灣路與石門東路,穿過第三應急避難所與第二應急避難所,穿過第一應急避難所。
穿過你們的身體,穿過你們的記憶。
回到森林的鸟
我在画小苹果树找医生,豆瓣电台就放到了这首歌。
今天起得早
心情特别好
梦里她对你招手笑
她住在城北边
那儿空气也不新鲜
你要带她去寻桃花源
街上真拥挤
汽车像蚂蚁
冒着黑烟排了几十里
有的在搬家
有的很调皮
紧紧抱着垃圾哭泣
幸亏你会飞
还不怕飞机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虽然有点慢
但用不着着急
只管舞动翅膀就可以
太阳高高照
没有沙尘暴
提起它你就害臊
妈妈对你说
她曾被吹跑过
睁开眼就到了外国
人生地不熟
也没有护照
呱呱叫着就要晕倒
爸爸救了她
还生下个娃娃
差点她就不想回家
请你继续飞
不要被干扰
干扰别人飞翔不是好鸟
不管他是谁
他拿着遥控器
或者他满嘴道理
飞过这烟雾缭绕的城市
也并不是那么容易
眼前的高楼
样子真奇怪
怎么绕也绕不开
你闯进一个奢华的房间
俩个人在争论明天
明天是他的
一个男人说
他有大炮和火箭
一个女人说“No”
明天是她的
她有这世界的一半财产
不要不服气
急了买了你
要不让你金融危机
他们在争吵
你趁机逃跑
要是被抓住还得了
你抖抖羽毛
松了一口气
但愿他们永远吵下去
终于看到
她飘摇的家
树奶奶已不再挺拔
她孤零零的站在那里
没有同伴为她遮风雨
风还没有吹
她就摇啊摇
像是城里人的老年操
向左摆一摆
向右摇一摇
还冲太阳挥手笑了笑
“小伙子 你好
欢迎你来到
快落在肩头歇歇脚
方圆几十里
没有几棵树
你这一路很辛苦”
她推开房门
一步飞过来
使劲在你怀里蹭她的小脑袋
说你怎么才来
你怎么才来
不来看我也该来看树奶奶
她活蹦乱跳
高兴的快疯了
说树奶奶你赶紧摇啊摇
树奶奶就摇啊
向左又向右摇
一下把他们摇回了森林
by 万晓利 《回到森林的鸟》
时候到溜
太阳落山的时候
下雨溜
燕子在屋檐下做了一个窝电视里的新闻说英国有十几万头疯牛
梦见他们都在草地上吃草
都在草地上吃草不知什么时候雨停溜
雨滴顺着树叶滑落地上
印第安人都从土里面长了出来
风一吹他们都跳起了舞学生去上学
工人去上班
宠物和机器在街上晒太阳不管明天刮不刮风 下不下雨
小燕子都要从窝里飞出去
时候已经到溜
时候已经到溜
by 吴吞《时候到溜》